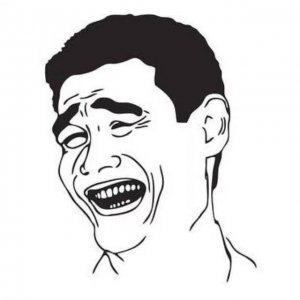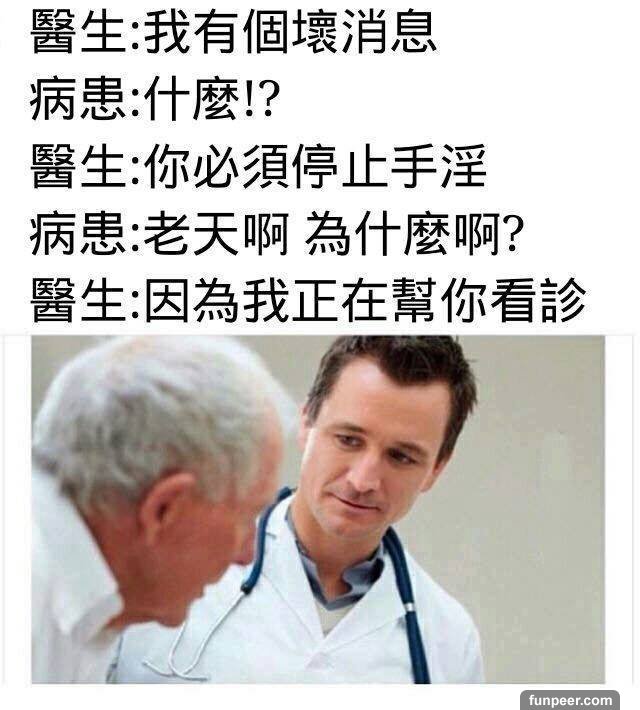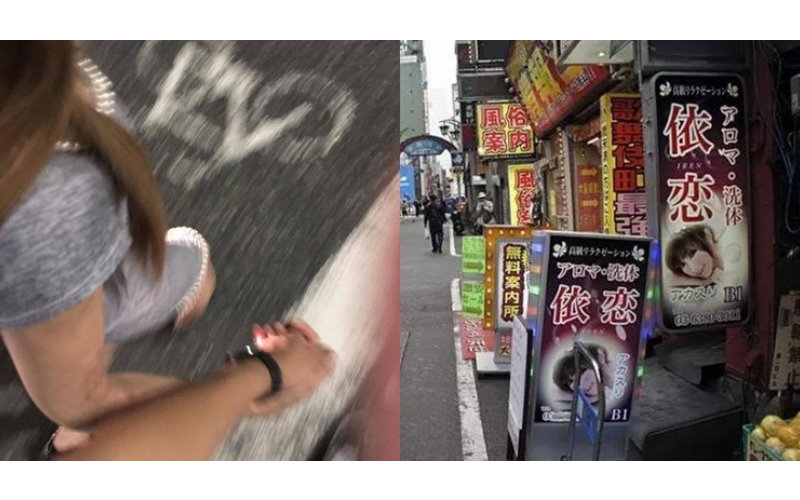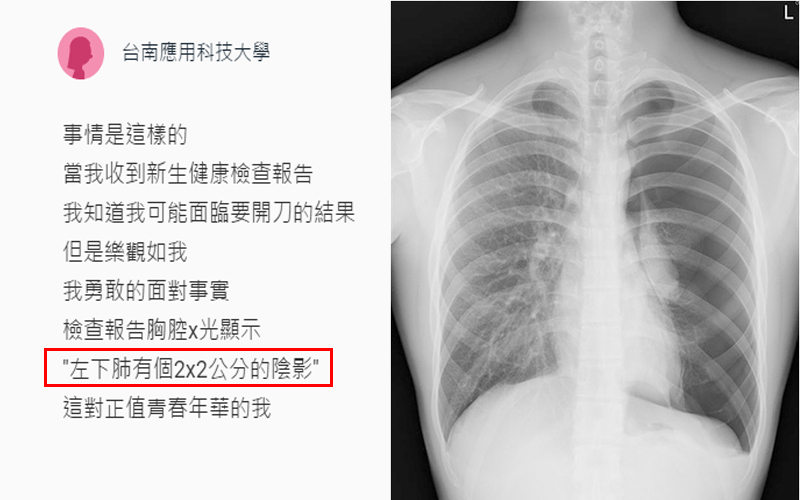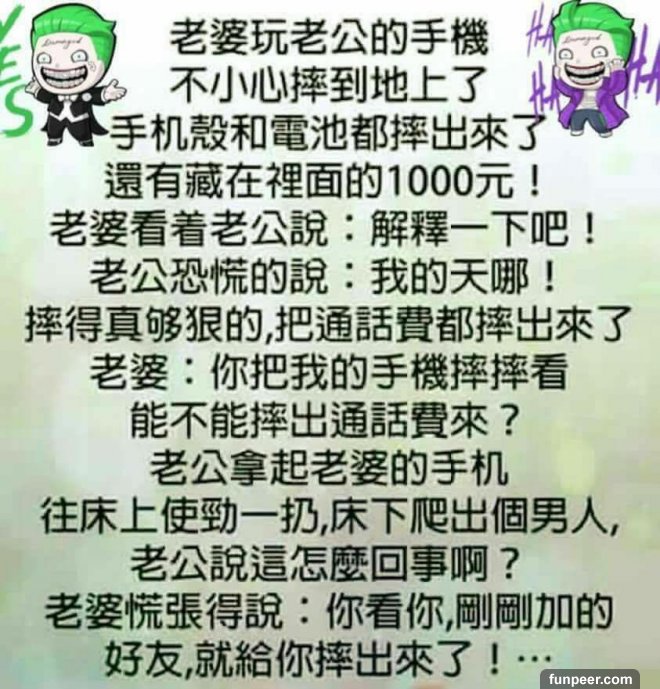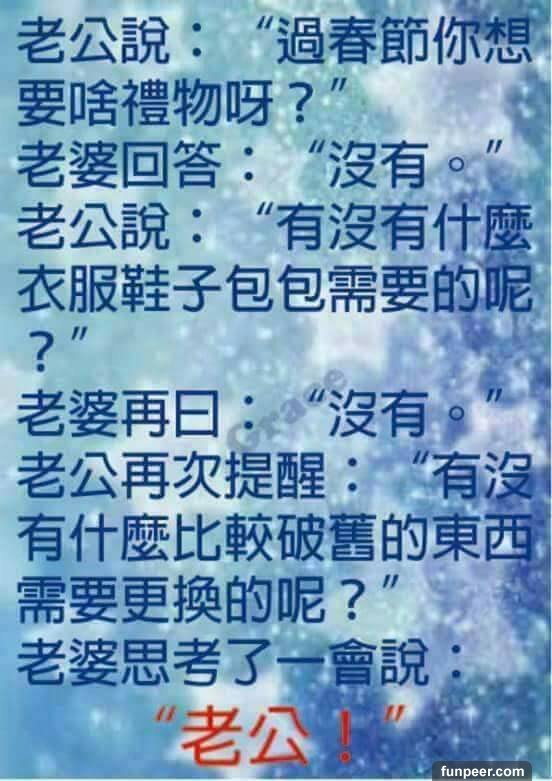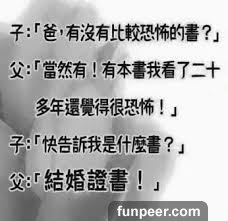係美國讀書時,見到個鬼妹"果度"濕曬,之後帶左佢入去爆房,估唔到鬼妹原來鐘意咁玩...


我叫Wesley,是一個在美國留學的香港學生。
我是一個DSE制度下的失敗者,
當年因為中文不及格,無奈之下唯有選擇到外國升學。
由於家境不算富裕的關係,
所以每逢假日我也會找份兼職,賺點生活費,算是減輕一下家裡的負擔,
而今日要說的這件事,就正正是發生在我假期裡當兼職的時候,
現在想起來,仍叫我心有餘悸。
到底內容是真是虛,相信各位看後自有判斷。
今年是我在美國渡過的第三個聖誕。
因為身邊的同學都相約一起去聖誕旅行了,
而我又不擅社交,兼之旅費太貴,
所以便答應了宿舍舍監的邀請,在學校當一個月的兼職,於工作中渡過聖誕。
我讀的大學名氣不大,位處偏僻山野之間,四周圍著的是大片叢林,
離最近的城鎮少說也有半小時的車程,簡而言之,就是一個很荒蕪的地方。
但正因為這裡如此僻靜,如此遠離繁囂,卻又使之成了渡假的絕好地方,

所以每逢暑假寒假,也會吸引不少旅客到來暫住數日,
而學校為了應付這個需求,便會把部分學生宿舍騰出,招待遊人。
我工作的地方便是在這些本來空置,新騰出來的宿舍。
由於我英文說得尚算流利之故,所以很幸運地被編了做接待處的工作。
工作時間在半夜,夜晚客人不多,
工作內容也就是接接電話,回答一下客人查問,說白了也不過是一份閒職。
我唯一的同事是個三十來歲的黑人,名作森姆,他是當保安工作的。
我們無聊時會一起在房裡打德州撲克,小賭怡情,時間好像會過得快一些。
森姆總是搶著當莊家的,他一手牌打得很好,

大的賭注他總是贏我,有次我說笑的問他是不是使詐了,怎麼都在贏我的錢,
他卻答我:「Wesley,你為人也太老實了,
單會說謊是不夠的,要騙得過人,先要把自己也騙得過去。」
我聽著不信,想撲克牌也不過是賭運氣,
只要拿著好手牌便是必勝了,結果當然是輸得一敗塗地,每晚也輸幾美金給他,
現在想來也有點後悔,根本打從開始就不應該跟他對賭。
sponsored
事情的開端發生在這麼一個夜晚,
我很記得這是我到來工作一個星期後的事,
這晚我如常的跟森姆在打牌,
這一盤我手牌很好,拿著一對ACE,很自然的便把賭注也押至十美金了,

森姆還在猶豫是否要跟注之際,卻聽外邊有人在拍鐵閘門:
「喂,有人嗎?」
說話的是一把女聲。
森姆聽後笑了笑,作了個很奸詐的表情,
我對他說:「別使詐,我這就回來,這局我是贏定的。」
他笑而不語,只是催促我出去應門。
那是個大約三十歲的婦人,
半夜裡仍戴著一副墨鏡,黑色圓頂帽,只露出了金色的曲短髮,
皮膚很白,白得全沒血色,可口紅卻塗了反差很大的鮮紅色,
我看到先是呆了呆,然後問:
「小姐你好,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她凝神看著我,隔了很久才吐出一句:
「我想Check-in。」
她說起話時語調的起伏不大,聲音很冰冷,叫人聽起來有種距離感。
「好的,你有訂房嗎?或者 … 」
她沒有答我,只是向我遞來顯示著電子帳單的手機。
sponsored
我如常的替她辦著登記的手續,可期間卻始終忍不住不停的偷看她,
在如此半夜要Check-in的人本就不多,她還要如此奇怪的打扮,總叫我感覺有點古怪。
「小姐有泊車嗎?」我又問。
「無,」她答,仍是聽不出絲毫語調的變化,
「好的,那麼請在這裡簽名,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你的房間就在 ... 」
我想快快把一切交代完,便回去贏了那場十美金的賭局,
那知那女人卻問我:
「可以告訴我這裡有安裝防盜攝錄機的位置嗎?」
我聽著楞了一楞,心想這問題也有夠古怪,但也不以為意,想了想便答:
「這裡是學生宿舍,外人不多,就只有這裡接待處和升降機有攝錄機二十四小時監察 ... 」
她沒聽完便回頭要走,走起路來時有點閃縮,而且不停的往四處張望,
好像在找著些甚麼,又好像在逃避些甚麼,
可走得不夠兩步,卻又見她慢慢停下來,回過了頭,
「先生,」她說。
「嗯?」

「我有點餓了,可以借十美金給我買吃的嗎?」
我聽著呆了呆,摸摸褲袋,答道:
「我身上剛好沒錢 ... 有的話一定借給你,不過你若是急著要現金時,那邊有提款機可以 ... 」
我正欲為她指出提款機所在的方向,可回頭再看時,卻已不見了她的蹤影。
「怪女人。」我在心中對自己說,然後便急著回去跟森姆賭錢。
開牌吧,」森姆笑說,
我再回去時已經見他把一張十元紙幣放在桌上,
桌上亮出的牌是A, 8, 3, 4, Q,
我再看牌面的花式,想森姆無論如何是贏不了這局的,
「多謝了,」我笑說,一邊已急不及待的拿下他的錢,
「這麼有信心,你手裡拿甚麼牌啊?」他說著翻開了我的底牌。
「哈哈,輸的是你,」他接著翻開自己的牌,是兩張Q,
「三張A怎麼也比三張Q大吧,」我笑說,
「你看清楚一點再說,」他指著我的牌,
我一看時,見自己手裡只餘一張A,另一張卻換成了K。
「這 ... 這怎麼可能 ... 你換了我的牌?!」我氣道。
「誰要換你的牌,這裡有閉路電視的,你不信自己回帶看吧,」
他笑說,一邊已搶下我手中的20元美金,然後站起來拍拍褲子:
「好了,差不多時間巡樓了,回來再打吧,」
我實在難以置信,森姆為人雖然從沒正經,可賭錢使詐的事他卻是不做的,
為求真相,我待森姆離去後立即就把影帶翻前一分鐘,
可期間只見森姆乖乖坐著不動,自顧自的按著手機。
時至今日,我仍然想不出當晚到底是森姆使詐,還是我累過了頭把牌看錯,
但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這一切都發生在當晚的凌晨三時正。
我對那一晚的事情印象很深刻,
一半自然是因為不明不白的輸了錢給森姆,但另一半卻是因為那古怪女人的事。

待森姆走去巡樓以後,我一個人在接待處無聊,便開始胡思亂想,
想的除了是牌怎麼給換了外,還有跟那女人的對話。
我都說過,我們學校的宿舍位處在一個很荒僻的郊野,離小鎮最少也有半小時的車程,
而最後一班往來的巴士是在凌晨一時的,也就是說,除了自己駕車以外,
在如此半夜是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從外邊進來的,
但我記得當我問起那女人有沒要泊車時,她卻答我說沒有,
那到底她是怎麼到來的?

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
難道她在山野之間徒步走上了數個小時嗎?
又抑或她不是孤身一個,而是另有接送她的人?
我越想越是離奇,卻始終想不出個答案,
待森姆巡過樓回來後,我有跟他討論過這個問題,
但他卻似乎不太感興趣,只叫我別管人家的閒事,繼續賭錢,
我沒有賭錢的心情,但想森姆說得不錯,也沒必要為此煩心,便打算讓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可當第二晚我再見到那個女人時,心裡的疑問卻又更多了。
我再見到那個女人是在第二晚森姆巡樓以前,也就是大概凌晨三時左右。
這晚我沒有和森姆在賭錢,只因昨夜的事仍叫我耿耿於懷,
非是我不信森姆沒有使詐,而是想自己手氣不好,精神狀態也不佳,
勉強賭來沒意思,便說要休戰一晚。
森姆聽後沒趣,但也奈我沒何,
便播起他很吵的Hip-Hop音樂,自顧自的和他的女友通電話。
我坐在接待處的櫃位,昨夜的事始終在心中縈繞不去,
我在閒時一向有寫小說故事的習慣,於是心血來潮便拿起紙筆,
把當中的細節記下,也就成了這段故事的初犒,
而這也是我現在仍能把每一細節如此清楚交代的原因。
正當我寫得入神時,忽聽大堂傳來高跟鞋走路時發出的「閣閣」聲,
我好奇仰頭一看,見是昨日那個古怪的女人,
她的打扮跟昨日無異,仍然是墨鏡,黑色圓頂帽,
可這夜遠看之下,見她原來身穿一件黑色的大衣,長度剛好及膝,
下面露出了一條青白無血色的小腿,好看是好看,但就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怪異。
我望著她的腳,見她一步一步向我走來,
走至大約離我兩米左右的距離便見她停下,凝神的看著我,
我被她看得很不自在,便回頭去找森姆,
「喂,森姆,你看,又是昨夜那個女人,」我悄悄踢了他一腳,
他沒理我,只冷冷看了那個女人一眼,便又繼續和電話中的女友說笑。
「先生,」
那女人隔著一段距離呼喊在櫃檯的我,我聽著只覺得好古怪,
「你還好嗎?有我可以幫你的事情嗎?」
我說著便站起身,打算走到她的身邊去,看她有甚麼需要。
「別過來,」她卻說,然後示意要我往上看。
我朝她所望的方位一看,見是那部置在接待處的閉路電視,
心中即時明白一點,想她是怕被攝錄機拍到。
「好的,我不過來就是,你有甚麼要我幫忙的?」我說,
「我想你幫我做一件很簡單的事,」她說,語調仍是不帶任何變化,
「當然,請說吧,」我答,
「以後若有人問起我時,請你說從來沒有見過我,或者就說我從來沒有在這裡出現過,可以嗎?」
她用戴著墨鏡的眼看著我,我實在看不出她到底在想甚麼,
但想這個要求雖是十分古怪,卻同時又非常容易辦到。
「這 … 顧客的隱私我們一向是很尊重的 …」
她沒耐性把話聽完,我才說至一半,就已見她步離了大堂,
在雨點飄雪之間點起一枝煙,然後消失在角落處的黑影裡頭。
宿舍地下這一層的設計很特別,
我和森姆在的一方是接待處,另一方則是通往房間的電梯樓梯,
大堂出入口置在兩側,各有一道落地玻璃,
也就是說無論從裡邊外邊,也能清楚看到另一端的情況。
我記得這晚的天氣很壞,外邊冷得都已經下起雪來,
那女人走到大堂外邊的一個陰暗角落抽菸,
她抽菸的位置離我在接待處的位置較遠,
我在裡頭除了能看見她吸菸時燃起的那點微弱橙紅火光以外,
也就只能隱隱看到她叉著手抽菸的身影。
我多看了兩眼,然後便又埋頭把這一節記在我的稿子裡。
沒待那女人把煙抽完,便見森姆掛上了跟女友在通的電話,
「我去巡樓了,」他對我說,「那女人呢?她找你了嗎?」他也沒認真在問,
「沒有,她不過問我那裡可以抽菸而已,」我答,說著便向森姆指指那女人正在抽菸的方位,
「哦,」他往那陰暗角落瞥了一眼,然後便拿起鑰匙簿子巡邏去了。
那女人大約在森姆走後十五分鐘回到大堂,
她走起路時仍如昨夜般的閃縮,不停的往兩邊出入口大門望去,
臨走至樓梯門前更加快了腳步,似乎真的在躲著些甚麼。
我看著只有越來越胡塗,
她不選擇乘升降機這一點倒不叫我意外,她是有意避開攝錄機監察的,
但其中的原因我卻怎麼也想不出來,
她是在躲著一個人嗎?
但她就算是躲,也大可不必躲開這裡的攝錄機,畢竟也只有森姆和我會看這些無聊的影帶,
而她又為甚麼要我別在人前提起她?
我就是連對她的名字也沒有印象,她要不是一舉一動如此的古怪,
我是斷不會把她的事放在心上,也就把她當作一個普通的住客而已,
但現在她這麼一說,反而叫我疑心更盛,
是有人要找她嗎?她開罪了甚麼人嗎?
這些問題我在心裡不停的問,不停的想,卻始終沒有答案。
想得累了,我便把接待處的大閘拉下大半,也到外邊抽一根煙放鬆一下,
我特意走到那女人剛才抽菸的角落處,見地上果然放著一個印有鮮紅色唇印的菸蒂,
但這菸蒂說來也十分古怪,古怪的是這支煙並沒有抽完,
總共只燒了四分之一左右,而周圍附近也找不到別的菸蒂,
那女人剛才在這裡足足待了十五分鐘之久,她是真的在抽菸嗎?
而地上這個印有唇印的菸蒂又真是屬於她的嗎?
我心裡又多了更多更多的疑問,
「想得太多了,」
我嘗試告訴自己,然後默默的把煙抽完。
我回到接待處時已見森姆巡過樓回來,
「抽菸去了?」他問我,
「嗯,」我點點頭,「你也要嗎?」說著向他遞過香菸,
「陪我再抽一根吧,」他拉著我陪他再抽一根,
這晚外邊的風雪很大,天色很暗,
我很想跟森姆討論有關那個女人的事,
但他似乎對此事不太感興趣,於是我也就不提了。
我對這一晚的事情印象很深刻,除了是因為和那女人很古怪的對話外,
亦因為這晚不過是往後一切的開端,
那女人打從這晚以後,每日大約凌晨三時左右,
也會穿著同一身裝扮,到同一個位置抽菸去,
很多次森姆也和我目擊她下樓抽菸的情況,
我有問過森姆覺不覺得那個女人每晚在特定的時間下樓抽菸很古怪,
他卻說有些人是喜歡有規律的生活的,
又反問我他每晚三時也要去巡樓是不是很古怪,
我一笑置之,沒有再跟他爭辯下去。
不過還有一點很值得提及的,
就是那女人每晚也會抽十五分鐘煙,不多不少,
而且每次在森姆巡邏回來以前便會回房了。
我對她的事很好奇,於是每晚待她抽過煙後,
我也會到她抽菸的位置去抽一根煙,
而我每晚看到的,便是地上多了一根印有鮮紅色唇印,只抽了四分一的香菸。
這個女人的事對我來說非常古怪,不過也就只停留在古怪而已,
一直到她在這宿舍住了一星期以後,事情終於開始有點轉變,
而我亦知道一切並不如我想像般簡單。
(待續)
[圖擷取自網路,如有疑問請私訊]
|
本篇 |
不想錯過? 請追蹤FB專頁! |
| 喜歡這篇嗎?快分享吧! |
相關文章
每日最熱話題頻道